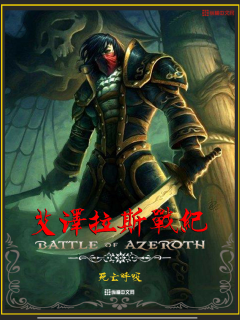生活就像一盒什么糖果,这话谁说的我忘了。
宫廷餐饮以甜为主,这能彰显国王的尊贵,而我想说你们的生活可不是糖果而是一盒调味品,咸的,辣的,苦的,酸的涩的,腥的臭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唯有甜的却很少见。
这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磕磕绊绊,走了那么远的路,见了那么多人,发生那么些的事,活到现在算幸运么?
幸运是甜的么?
我想应该是。幸运让人高兴,吃甜的也让人高兴。
在吃了很多酸苦辣辛咸之后,再吃到嘴里的那点甜就会让人尤其高兴。可最怕的是吃完了酸苦辣辛咸之后等待你的是腥臊馊涩臭。
被像死狗一样丢进一间屋子里。
没有柔软的床铺,没有女人的抚慰,我似乎失去了柔软床铺的使用权。
房子里没别的任何东西,只有这张铺着茅草的床。茅草在床上,我在茅草上。武器和包裹就这样被扔在地上。他们还是很体贴的。
衣服破了,透过被抽烂的衣服被鞭子抽过的痕迹清晰可见,被群殴时造成的淤青历历在目。脸上包着的绷带告诉我伤得不轻。
据说头老是被撞击会得痴呆,可我担心的是还没等痴呆就被毁容了,虽然我个人确实没那么英俊,但要是被毁容了岂不更惨。
门从外面被锁住了,这个处境我不知道该往哪方面想。
正在发呆的时候屋门被打开了,一个干瘦老头推门走了进来。
“你醒了。”他手里空空如也。
“我晕了多久?”
“一天一夜。”
“谢谢你救了我。”
“你更该感谢金钱。”
“我现在哪?”
“塔伦米尔。”
我起身就想走出屋子,被老头一声叫住,“你最好别出去。”
“为什么?”
“前两天莱塔村整个村被屠,现在到处贴悬赏抓土匪,整个塔伦米尔镇人心惶惶,卫兵跟疯了一样四处盘查,且不管是什么原因把你搞成这样的,你只要出门必定会遭到盘问,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吧。”老头看着我说道。
我还是好奇地趴到门缝上往外瞧。
“你可以出去,但我不保证你能回来。”老头出门端进来一个锅,他将草药倒进一个锡罐里一边调草药一边问:“是哪个家伙把你打成这样的?”
我回头看着老头说:“嗯……口角。”
“呵……”老头挑了挑眉毛瞥了我一眼。
“你可以不用锁门的。”他给我换了药离开时我赶忙说道,老头理都没理我直接锁门走了。
屠村……
老头的话叫我回忆起了那晚发生的事情。
说实在的我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现实。我觉得学到一些本领就能怎样怎样飞黄腾达,可最后来了这么个活。
如果是打架斗殴我觉得我做好准备了,可搞屠杀这种事我是真没一点心理准备。
村民不是敌人,至少我不认为他们是敌人。那个尸首分离的女孩是敌人么?她有什么错?那些手无寸铁的村民有什么错?
忽然门外有个人影闪过门再度被打开,艾丽莎站在门口看着我。“好点了吗?”她关上门走到我面前。
“唔。”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看了她一眼。
“嗯,看上去确实好些了,应该能骑马了吧。”女人弯腰凑近看了看我的脸说道,“今晚你得离开这了。”
“去哪?”
“你可能还得恢复一阵子,或者……嗯……也没那么多时间了,但你不能在这里待着了,毕竟你也没能完成你的工作。”
“是屠杀那些平民吗?”
“都是必要的牺牲。”她的脸上写满了平静。
不敢相信这场屠杀从她嘴巴里吐出来竟然如此轻易。
“那个村子的人跟你有仇么?”
“没有。”她看着我的眼睛。
“还是跟拉文霍德有仇?”
“更没有。”
“那跟谁有仇?”
“跟谁都没仇。”女人的眼睛其实挺好看。
“那就把他们都杀了?”
“必要的牺牲。”女人直起了身子。
“我不愿意屠杀那些手无寸铁的人。”
“好的,所以下次他们都会带着武器的。”女人说,“这个好办。”
“啊?”
我听迷糊了,你听你迷糊么?
“你什么意思?他们不是农民么?为什么要屠杀无辜的平民?”
“没有谁是无辜的,也没有谁不是无辜的。”女人伸出她的手指挑起我的下巴。“你还没有选择的权利。”
“据说你是暴风王国的人?”她岔开了话题。
“怎么?”
“温斯顿说要特殊关照你,他希望你好好配合。”女人的话叫我皱了皱眉头。
“那晚算是特殊关照么?”
女人没理我,“你现在不再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外乡人了,你现在是奥特兰克王国凯尔达隆郡冰封村的一个……嗯,你以前会干什么?”
“石匠。”
“那就是一个石匠。”她说。
“你的领主名字叫巴罗夫,阿比盖尔•巴罗夫公爵大人。”她认真地看着我,“你记住了么?”
我点头。
“你们镇的领主是瓦利玛·莫迪斯男爵。”
“什么男爵?”
“瓦利玛·莫迪斯男爵。”
“这是为了谁杀人?是巴罗夫还是……”
“闭嘴!”女人的脸一下子严肃了起来,“管好你的嘴,如果你再这样,你可能不会死,但一定会变哑。”
我咬了咬牙。
“不需要你知道的,你就不要问,与你无关的事,你也不要打听,做好你的事收好你的钱。知道的多了,不是好事。”她的睫毛很长,眨眼的时候带着一丝性感。
“还有,我希望你以后学会礼貌,这必须要养成习惯。”女人挑了我一眼。
“我哪有错。”
“是巴罗夫公爵大人,公爵……大人!”她加重了语气。“你没接触过贵族不懂礼貌我暂时不会怪你,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得改,你还要做很多事情,不仅仅当个地痞流氓去杀人抢劫。”
“好吧,即使不管是为了巴罗夫还是为了谁,那晚行为是被谁允许的?”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菜鸟,这是我说的最后一次,所有的事都不是你能怀疑的,你要牢记你的身份,做好你的事,然后活下去。还有,你最好对巴罗夫公爵尊敬一点,或者干脆闭上嘴,尤其是还有旁人在的时候。孤狼说你有些天赋,我只希望他没看走眼。”女人的眼神变得有点凌厉
“我知道你想当个所谓的好人,呵,但我希望你千万别给自己找麻烦,更别给巴罗夫公爵找麻烦,尤其是别给拉文霍德公爵找麻烦。”她的语气很严肃。
这算是威胁么?
“我他妈……”
“喔……闭嘴,比尔!谨言慎行,当心你的小命。”
你他妈的!我他妈不干啦!
当天晚上我就被送出了塔伦米尔,究竟去了哪里无法可知,只知道最后落脚到了一个小农庄。
第二天清晨一大早被嘈杂的吵嚷声吵醒,竟然是那晚一起去打劫的那群人。那个角盔男我是不会认错的。
他们怎么也在这里?
睡是没办法继续睡了,带着一肚不满我走出了屋子。
“看啊,看这是谁来了!”有人大笑起来。
“哎呦,果然是那只菜鸟。”
“看那猪头。”
“是那头猪。”
我忽然想起了冬幕节那天。
我识趣地想要坐到一边,可还没坐稳凳子被一脚踩歪,我一屁股摔到地上。
冤家他妈的路就是窄,扭头一看是那晚带角盔的家伙。此时终于看清了这家伙的长相,脸上的一道伤疤让他本来就跟窝瓜一样的脸更加令人恶心。地包天的下嘴唇和露出的牙齿跟狗一样。
“这地方不给懦夫坐,滚到另外一边去。”那家伙咧着嘴说话时我发现他嘴里少了两颗门牙。
从地上爬起来我狠狠瞪着他,“你想死么?”
“噢哟!看见没!这菜鸟几天不见脾气倒是很有长进!”这男人走到我面前用脑门顶着我的额头挑衅道。“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伤的就这么算了的,不过看来你似乎没事了。”
猛一伸手将他推了出去,“你嘴巴里面味道很臭你自己不知道么?”
他脸上瞬间写满了惊讶,然后玩笑似的对我说:“看来你恢复得不错啊,嘴巴都利索多了。还是那晚把你打傻了?”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面对这个家伙我原本不想把矛盾升级可他得寸进尺那就不能不收拾他了。
“反正大家闲着也是闲着,陪你玩玩。”他歪着头摆出了进攻的姿势。
看着他的下巴我是越看越觉得不顺眼,我直接踏步迎了上去。
他张开双手朝我胸前抓来。那略显散漫的出手表明他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我直接抬腿给他肚子上一脚直蹴,他一下跪在了地上。
左脚往前猛迈一步我高高扬起了手,他抱着肚子一抬头的功夫我的巴掌了落了下去。非常清脆的一记耳光,“啪!”他扭身趴在了地上。
我没有继续殴打他,而是站在他面前等他再抬起头来。
不知是经常打架的人抗击打能力要强得多,还是他觉得受到了侮辱才这样,他一骨碌爬起来奔着我就扑来,我不会像野狗一样跟他贴在一起撕咬,这太没水平。
先耍耍。
当他被我彻底激怒却对我无可奈何的时候他拔出了刀子,他迫切地想给我放放血。
我将目光投向其他人,那些人看我的眼神变得不一样了。没有鄙夷和不屑,嘲讽变成了仇视。
他们越这样我打的那家伙就越狠。他的脸被我抽肿了,在把他的牙再掰下来几颗之前我不准备停手。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是那晚那个大个子光头。他朝我撞了过来,接住他的胳膊我猛退两步,一伸脚被我绊倒摔在了地上。
这家伙跟狗一样腰上一拧一骨碌又爬了起来,他显然记住我刚才怎么扇那家伙的了。
这俩人一起上了,光头膝盖被我踢了一脚之后歪在地上,地包天被我迎面一拳打掉了一颗牙齿。
地包天捂着嘴叫唤的时候我三步并做两步一个侧身弓步上前,胳膊肘直接顶进了他的怀里,只听他胸前一声闷响,他整个人飞了出去。
倒地之后他抱着胸抽搐了起来,然后就不动了。
瞬间周围安静了下来。
光头男跟他的关系应该不错,看到同伴不动了他疯狗一样朝我扑来,可他抓不住我,无能狂怒只会让他的进攻更没有效果。当他从架子上抽出一柄长剑的时候他眼里已经不是杀气,而是疯狂。
长剑容易躲,但不容易近身。
菜鸟们,教学时间。等你上了战场遇见手持双手剑的敌人,一般都是重甲兵,离他们稍微远点,不用想着消耗他体力之类的事情,你做不到,而且他们一旦靠近你,你几乎就要死了。
即便是没有身着重甲但是使用双手剑的士兵也不要掉以轻心,毕竟能伤人的可不光是剑尖。
连续闪过两下攻击后就我就知道他水平如何了。他的节奏他的领域可以被我轻松打破。而一旦进入我的领域之后,他的生死就是我说了算了。
捡起地包天的匕首我朝他贴了过去,往左一个虚晃,紧接一个停顿,我给他留了反应时间。
留这个反应时间纯粹是为了迷惑他,我太知道他脑子反应过来之后会做什么了。
所以我没有选择往右晃身子而是继续往左。
此时离这个家伙还有一步半,我看向了他的脸,他的眼。他惊异的眼神告诉我他知道自己的破绽已经露出来了,他一定感觉到危险了。
边上有人大叫了起来,看来周围的人也不傻。
他的眼神说明了一切。
其实这一刀只要刺出去他一定死的,但我选择了收手。
剑划过他的肋间,我一个翻滚撤出了他的攻击范围。
殷红的鲜血出来了!“你的动作跟脑中风后半身不遂的人一样缓慢。”我朝他吐了一口唾沫。
我要慢慢的,慢慢地给他放血!
没有人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当然我也没兴趣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估计你大概也不会有兴趣知道一具尸体名字叫啥,多大年龄,有没有老婆,有几个老婆,他妈是谁,他爸是谁,他爱吃土豆还是爱吃西红柿。
你不会。
所以我也不会。
恼羞成怒!对!他张开大嘴嚎叫着!眼神里有诧异,有愤怒。不得不说他那口大黄牙!上面的牙结石我都看到了!
他大叫着举剑朝我再次劈来的时候我决定把他的下巴卸下来。
此时身体整体感觉相当好,这狗东西扭动的身姿,圆睁的双目,张大的嘴巴,喷出的口水,收缩的肌肉,飞扬的头发,这一切都像慢动作播放一样被我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脖子也露出来了……
他一剑劈下,我一个左闪身,匕首轻轻地搭在他的剑身上,此时能真切地感觉到武器接触后的产生的碰撞和摩擦,匕首顺势向上滑出!
刀锋朝天!
那裸露的脖子上暴露的青筋一会将要喷出血,红色的,暗红色的,或者是黑色的!温热的……血!
内心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插!插进去!
“住手!”拉尔夫爆喝。
不!不能住手!谁都不能阻止我住手!这人该死!他死有余辜!他可以死!他必须死!
这感觉好极了!就像高潮前的冲刺!冲动!冲动!快!快!再快!
他的脖子上会鲜血喷涌,血花四溅!
突然我身体被狠狠撞了一下,一下失去了平衡!猛打一个趔趄,我站住了。
一只手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这感觉似曾相识。很不好,我猛地甩开,他没有抓住我。这力量跟法拉德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挣脱束缚后我猛往一边闪了出去。
是拉尔夫,他的眼睛里满是愤怒和诧异。
“可以了。”他说。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盯着他的眼睛!
“哈,前几天我在地上的时候你也这么说过么?”我的眼神完全挑战他。“是不是那晚也是你说可以了他们才住手的?”
“我还没输!”那个狗东西大喊。
“闭嘴!”拉尔夫朝他吼了一声,“你们这群垃圾都给我回屋里去,吃完饭立即出发!”
地包天被拖进屋里,他没死,如果死了就直接盖上草席了。尽管没死可我能保证他至少一个月之内不能骑马挥剑。对于这点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早饭我没吃,不是不想吃,而是混着尿的食物或许动物才会吃。
我没有把碗摔在他们餐桌上,那几个一直朝我瞟的人我记在了心里。来日方长。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到处转移,跟他们的接触中有些人对我的态度还行,而那几个上了我黑名单的家伙能明显感受出对我还抱有敌意。
不过没关系,有的是机会。
这都是小事,而从他们口中我得到的最奇怪的消息是他们这群人压根不是巴罗夫公爵家的内部武装,甚至连“拉文霍德”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他们的表情不像是骗人。而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慢慢混熟了我才知道这群人以前压根就相互不认识,他们是从各地被招募来的,而且在各地时这些都是些泼皮无赖地痞流氓,甚至还有逃兵和雇佣兵,又洛丹伦人,吉尔尼斯人,斯托姆加德人,甚至还有库尔提拉斯人。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被召集到一起也刚没几个月,他们被分散在各个地方,没有任何行动就是不断更换驻扎地点,那次屠村是他们被召集起来那么长时间的第一次行动。
当然了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抢劫,然后分钱,他们大部分人以前都背着命案或者重大案件,杀人这种事他们是不惧的,但他们也说还是尽量不要滥杀无辜,毕竟杀人这种事可是大事,一旦被并案追捕很麻烦。
然而那次行动他们说他们也很诧异,他们是杀过人,但没有参与过屠杀。可一旦看到人多了,场面乱起来了,见了血了也就没人在乎了,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杀了人。
他们纵情抢劫,而要求也只有一条不留活口。如果不是时间有限,他们是很想强奸几个女人或者男人。而那一晚从进去到出来总共也就不到半个小时。
当问到他们的首领是不是拉尔夫的时候,得到的确切的消息是他并不是首领,可问起是谁的时候他们却都说不知道,他们见过拉尔夫曾对一个人相当恭敬,但也不确定他是不是首领。问他们那人长什么样他们也说不出来。
我问他们是不是个女的,长得挺漂亮的一个,他们说不是,那是个男的看不到脸。至于那个叫甘尼斯的家伙他们说应该是个头领,据说很多人都是投奔他来的,但那个人比甘尼斯高多了。
在他们嘴里甘尼斯那家伙是个十足的恶魔。而拉尔夫,听说他以前当过一段时间刺客。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拉文霍德,所以也不用再问下去,究竟拉尔夫是不是拉文霍德的人搞不清楚,但猜测应该是,毕竟他知道孤狼这个人。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再看他的时候虽然依然带着些许的不满,但已不再有那种时刻想弄死他的那种愤恨,只不过有时候我想问问他冬幕节的那天他在不在场。
转眼又过了两周多,这天傍晚被通知晚上要有行动让我们提前准备。
当看到那个光头的时候,他正恶狠狠地盯着我。我朝他笑,笑得很不屑。
那一夜的情景不禁又浮现眼前,一个不是很好的念头出现脑海里。
“这次行动你知道干什么吗?”出发前拉尔夫过来问我。
“你安排。”我瞥了他一眼。
“那我安排的是什么!”
“听你指挥。”
他哼了一声之后转身走了。
这次又是跟着来到一个村外,但这次似乎走得更远些,人依然还是那群人,只不过这次没有任何的外围埋伏,而是直接冲进了村里。
不一会村子变成了炼狱。
我没有参与杀戮,只是像一个孤魂游荡在燃烧的村子里,徘徊在撕心裂肺的呼喊和哭嚎中。
那个天杀的大个子拽着一个女人的头发把她拖进了屋里。不光是他,还有很多……
看!有个家伙挑着一个人的头颅边跑边笑,一个被一剑刺穿的老人倒在了路边。一个被砍掉的头颅被人一脚踢出去老远,那脑袋翻滚着,血从切断的创口上洒了出来。
在火光的映照中,那狰狞的,扭曲的,痛苦的,悲伤的,惊恐的面容不停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不管是睁着眼还是闭上眼,那一张张不同的脸出现在我眼前。
蹲在一具尸体边我打量着她,不,她还活着,只不过快死了,血从她的肚子里流出来,她的脖子也在流血。
我撩开了她的头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她茫然地看着我,没有惊恐,没有悲伤。
她张了张嘴巴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然后慢慢地不动了。
她死了。
不远处的路上一个被按倒在地的女人发出的不是呻吟而是惨叫和哭嚎,压在女人身上那个咬牙切齿的家伙疯狂地扭动着身体。
一种极度的厌恶和愤怒以及一种无法言喻的悲伤情绪瞬间充斥了我的内心。
听着旁边屋里传出女人的哀嚎,我抽佩剑抬脚猛地踹开了屋门。